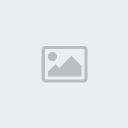苏南是个有报恩情结的人,苏南的前任贴身秘书离任时,曾对温朴有过细致交代,让他日后在白家的一些具体难事上,替老首长多操些心,并告诉温朴,过去他的两只手没少拎彭青家的愁事,给彭青的子女找工作、落户口、调房子。后来白石光辞职做生意那几年里,老领导也没少用电话关照白石光的生意,还批过两次条子。
温朴做苏南贴身秘书这几年里,白石光倒是没怎么给他添麻烦,一些小来小去忙,温朴抬抬手也就帮下来了,甚至有时都不用惊动苏南。白石光近几年的行动轨迹,温朴还是能描绘个八九不离十。一心想干出名堂的白石光,辞职后掖把牙刷四海为家,活得很写意,也挣到了一些钱,适时回东升开了一个贸易公司,起初生意还过得去。不过后来温朴听说,他跟人合伙到黑河做边贸生意失了手,被骗走了八十多万,还差点把命扔在那边,回来后就把公司改成了游戏厅,人活得很蔫相,温朴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三个月前。
一天中午,苏南下车时摔了一跤,倒地后起不来了,送医院一检查,骨头没伤着,就是脚跟筋蹩了一下。当晚,白石光也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,匆匆从东升赶到北京,怀里抱着一个超大花篮,说是代表他母亲来看苏伯伯。白石光没吃晚饭,苏南就让温朴领白石光出去吃饭,替他好好招待一下白石光。路上温朴问白石光想吃什么,对北京烤鸭有兴趣没有。白石光一听烤鸭,脖子就梗了一下,连忙摆手说,吃窝头大饼子都行,只是千万别吃什么烤鸭,沾鸭边的东西,甭说吃,我一听就想吐。温朴问他为什么,白石光就说他有恐鸭症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恐,恐到骨子里去了。
白石光就给温朴讲了一段有关鸭子的往事。
那一年,刚二十出头的白石光,伙同几个哥们去老家洼子淀偷猎野鸭子贩卖。洼子淀那边有人接应,搞了两条木船。在淀中心一带,他们遇上了成群结队的野鸭子,一散砂枪打出去,飞离水面的野鸭子,就成双成对地往下落,天晓得那一年的野鸭子怎么那么多,像是全淀的野鸭子都集中到了淀中心,召开第几几次洼子淀野鸭子代表大会,听老鸭王作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报告,然后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洼子淀野鸭领导班子和首领,那场面太壮观,太刺激人了,至今让白石光的记忆都没办法安静下来。白石光说,那天他负责往船上捞落水的野鸭子,死的不费劲,顺手一扔就进了船舱,而那些要死不活、乱蹬乱抓挣扎的伤野鸭,就得处理一下才能扔进船舱。处理手段说来也简单,就是两手抓住野鸭脖子使劲一拧,鸭脖子咔嚓一声折断,生死问题,眨眼间解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野鸭子不停地在枪声过后落到水面,随着体能的下降,白石光处理野鸭子的速度明显不像一开始那样有节奏了,两只早已被鸭血染红的手,一过度发力就痉挛,心口还怦怦颤跳,已经有无数只受伤的野鸭子从他手上逃生了。接近晌午的时候,血腥的猎捕还在继续,猎捕的疯狂快感还在枪手身上每一个细胞里跳跃着,白石光要求换换工作,不想再拧鸭脖子了,他要去放几枪,但放枪的人,这时却很难放下他们手里的枪,白石光的要求等于放屁。头晕眼花,天昏水暗,白石光的两只手,麻木得几近失去知觉,从水里捞死鸭子都要使出吃奶的劲来。同伴看他把受伤的野鸭子都放走了,就大声埋怨他手上利落些,别跟个老娘们儿似的磨磨叽叽,水面上漂的可都是钱啊!白石光骂了同伴几句,接着脸上一要强,鼓了鼓劲,继续拧野鸭脖子。后来白石光的两只手实在不中用了,只好趴在船帮上,捞到半死不活的野鸭子,就用牙来咬脑袋,咔叭一只、咔叭一只、咔叭一只……白花花的野鸭脑浆和腥红的野鸭血在他嘴里揽和后,变得黏稠了,顺着他的两个嘴角,不停地往外流,后来一个放枪的同伴,见他脸相如此残忍,吓得眼睛都瞪直了,结结巴巴地说,石光你来放几枪吧,我去拧鸭脖子。然而这时的白石光红眼了,可能也有点走火入魔,已经不觉得累和恶心了,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捕猎机器,捞到野鸭子,不管死活,一律咔叭咔叭地把脑袋咬碎,以至于到后来收场时,他那张脸,简直都没法看了,血糊漓啦的……
温朴做苏南贴身秘书这几年里,白石光倒是没怎么给他添麻烦,一些小来小去忙,温朴抬抬手也就帮下来了,甚至有时都不用惊动苏南。白石光近几年的行动轨迹,温朴还是能描绘个八九不离十。一心想干出名堂的白石光,辞职后掖把牙刷四海为家,活得很写意,也挣到了一些钱,适时回东升开了一个贸易公司,起初生意还过得去。不过后来温朴听说,他跟人合伙到黑河做边贸生意失了手,被骗走了八十多万,还差点把命扔在那边,回来后就把公司改成了游戏厅,人活得很蔫相,温朴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三个月前。
一天中午,苏南下车时摔了一跤,倒地后起不来了,送医院一检查,骨头没伤着,就是脚跟筋蹩了一下。当晚,白石光也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,匆匆从东升赶到北京,怀里抱着一个超大花篮,说是代表他母亲来看苏伯伯。白石光没吃晚饭,苏南就让温朴领白石光出去吃饭,替他好好招待一下白石光。路上温朴问白石光想吃什么,对北京烤鸭有兴趣没有。白石光一听烤鸭,脖子就梗了一下,连忙摆手说,吃窝头大饼子都行,只是千万别吃什么烤鸭,沾鸭边的东西,甭说吃,我一听就想吐。温朴问他为什么,白石光就说他有恐鸭症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恐,恐到骨子里去了。
白石光就给温朴讲了一段有关鸭子的往事。
那一年,刚二十出头的白石光,伙同几个哥们去老家洼子淀偷猎野鸭子贩卖。洼子淀那边有人接应,搞了两条木船。在淀中心一带,他们遇上了成群结队的野鸭子,一散砂枪打出去,飞离水面的野鸭子,就成双成对地往下落,天晓得那一年的野鸭子怎么那么多,像是全淀的野鸭子都集中到了淀中心,召开第几几次洼子淀野鸭子代表大会,听老鸭王作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报告,然后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洼子淀野鸭领导班子和首领,那场面太壮观,太刺激人了,至今让白石光的记忆都没办法安静下来。白石光说,那天他负责往船上捞落水的野鸭子,死的不费劲,顺手一扔就进了船舱,而那些要死不活、乱蹬乱抓挣扎的伤野鸭,就得处理一下才能扔进船舱。处理手段说来也简单,就是两手抓住野鸭脖子使劲一拧,鸭脖子咔嚓一声折断,生死问题,眨眼间解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野鸭子不停地在枪声过后落到水面,随着体能的下降,白石光处理野鸭子的速度明显不像一开始那样有节奏了,两只早已被鸭血染红的手,一过度发力就痉挛,心口还怦怦颤跳,已经有无数只受伤的野鸭子从他手上逃生了。接近晌午的时候,血腥的猎捕还在继续,猎捕的疯狂快感还在枪手身上每一个细胞里跳跃着,白石光要求换换工作,不想再拧鸭脖子了,他要去放几枪,但放枪的人,这时却很难放下他们手里的枪,白石光的要求等于放屁。头晕眼花,天昏水暗,白石光的两只手,麻木得几近失去知觉,从水里捞死鸭子都要使出吃奶的劲来。同伴看他把受伤的野鸭子都放走了,就大声埋怨他手上利落些,别跟个老娘们儿似的磨磨叽叽,水面上漂的可都是钱啊!白石光骂了同伴几句,接着脸上一要强,鼓了鼓劲,继续拧野鸭脖子。后来白石光的两只手实在不中用了,只好趴在船帮上,捞到半死不活的野鸭子,就用牙来咬脑袋,咔叭一只、咔叭一只、咔叭一只……白花花的野鸭脑浆和腥红的野鸭血在他嘴里揽和后,变得黏稠了,顺着他的两个嘴角,不停地往外流,后来一个放枪的同伴,见他脸相如此残忍,吓得眼睛都瞪直了,结结巴巴地说,石光你来放几枪吧,我去拧鸭脖子。然而这时的白石光红眼了,可能也有点走火入魔,已经不觉得累和恶心了,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捕猎机器,捞到野鸭子,不管死活,一律咔叭咔叭地把脑袋咬碎,以至于到后来收场时,他那张脸,简直都没法看了,血糊漓啦的……